阿母的目屎
新聞報導 - 自由論壇
作者 陳水扁總統
2012-09-12
八十五歲的阿母老了,不僅白髮蒼蒼,齒牙動搖,左眼則早已看不見,右眼亦視茫茫,我很擔心阿母一不小心跌倒將很麻煩。二○○九年阿母來北所看我,隔著桌子,竟然沒看到她的兒子就在眼前。沒多久,岳母也被蔡守訓合議庭叫去問話,回去之後,岳母問大舅子吳景茂為何沒看到我?吳景茂說:「水扁(ㄆーㄢ)仔就坐在您的左前方啊。」
兩個媽媽,一個深夜常為我哭泣,眼睛都哭瞎了;一個罹患失智症,常把兒子誤認為夫婿,到庭作證也認不出近在咫尺的女婿,蔡守訓們卻還不放過!
在這裡,除了不離不棄的阿扁們及情如手足的昔日同志好友外,家人是最大的精神慰藉,堅信當所有的人都離我而去時,在孤燈的暗夜裡,還願下來伴隨黑獄孤影的一定是親人。二○一○年五月八日母親節前夕,我透過掌上型數位電視聽到「扁媽的呼喚」,台上的阿母流不止的眼淚,讓我幾度激動抽搐淚流滿襟,兒時回憶一一浮上心頭。靈感一到,匆匆寫下〈阿母的目屎〉,本想敝帚自珍,後來被「台灣國寶」王明哲老師獲悉,幫我譜曲,收錄在《獄中之歌》的CD中。
阿生、章天軍主持的《台灣人俱樂部》廣播節目,三不五時有人點唱〈阿母的目屎〉這首歌,每次聆賞,每次都熱淚盈眶,不只為我唱出滿腹的思母之情,也是對我最摯愛的台灣母親的禮讚。
想起我細漢的時/阿母揹阮去園內抾番薯/先予豬食有賰換冰枝/糴米欠數寫佇壁門邊/若像阿母教阮學認字/;想起我大漢的時/阿母看病無錢問童乩/ 只有勤儉讀冊搶頭旗/為著台灣撩對政治去/毋甘阿母規瞑目屎滴/;阿母啊!阿母,你著毋通吼/你愛勇健等我平安倒轉去/叫你一聲:我比啥人較愛你/叫你一聲:我比啥人較愛你/我比啥人較愛你,較愛你……/。
王明哲從事歌曲創作三十年,在民主道路上,他以歌聲為矛,以文字為盾,激勵人心,鼓舞士氣。在街頭運動的狂飆年代,我特別喜歡他的〈海洋的國家〉和〈台灣魂〉。我擔任國家文化總會會長時,王明哲的〈台灣〉入選首屆的「台灣之歌」,我有幸與王明哲結緣。並在二○○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南下高雄他的家中拜訪,他彈著吉他,一起合唱〈台灣〉,台灣是生咱的所在/感念感恩在心內/付出情意付出愛/代代花蕊代代栽/。顯然比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」的〈國歌〉好唱好聽多了!
我喜愛台語老歌都是我小時候寒暑假到外婆家,和小我一歲表弟玩在一起的共同娛樂。舅舅家裡有許多台語歌本,我們一首唱過一首〈星星知我心〉〈採檳榔〉〈孤女的願望〉〈舊情綿綿〉〈悲情的城市〉〈溫泉鄉的吉他〉〈黃昏的故鄉〉〈可憐戀花再會吧〉……。後來選市長、總統,我極為重視競選主題曲,那是最直接,也是最能憾動人的選戰文宣,一首好的競選主題曲是選戰成功的一半。
感謝本土音樂創作者王明哲的鼎力相助,並邀來當年仍就讀波士頓大學研究所的賴彥霖與製作《獄中之歌》CD專輯;還有留學維也納大學博士班的劉莉莉老師,為〈阿母的目屎〉編寫四部合唱曲譜,替歌曲注入新生命。另外也要感謝自幼雙眼失明的陳秀綿,她有感於〈阿母的目屎〉歌詞中的兒時記憶與求學毅力跟她很相似,兩度從北港到台北錄唱唯一的女聲版。好友阿生、章天軍連袂為〈阿母的目屎〉灌唱,特別是章天軍自費權製〈阿母的目屎〉,以他感性的獨特唱腔,充分掌握我內心的底蘊,深刻詮釋我對阿母的感恩感念,及對台灣的吶喊,章天軍簡直是我的分身。
我出身佃農之家,只有一分多的農地,輪種稻米、甘蔗、番薯,收入微薄,無以維生。父親只能打零工,幫人插秧或甘蔗收成時協助捆綁,終年勞碌,卻寅吃卯糧。平常柴米開銷都先賒欠,註冊的錢則借高利貸,阿母用粉餅寫滿阿拉伯數字的牆,則是家裡的帳單,也是我小時候學習識字的最佳教材。
我也是勞工小孩,父親後來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,是鄭姓地主的男傭,任人差遣,不但到養豬場餵豬,也到農場噴灑農藥。長年未戴口罩的後果,是未滿六十歲就死於肝癌,看遍多間南部的醫療院所,都說是胃炎,北上求醫,確診為癌末,不到四個月就往生了。
外曾祖父重男輕女,阿母念到小學三年級便輟學當女工,嫁到陳家,整天為三餐不繼在操勞,全家六口同睡一張木床。阿母告訴我她常揹著我到田裡幹活,她汗流浹背,我也全身濕透乾脆在田埂旁挖個洞,當作我年幼時的搖籃,我是吃台灣泥土長大的孩子。
阿母不識之無,從小教導我窮要窮得有志氣,非己所有,不貪不取,到田裡揀拾地瓜或稻穗,必須是地主不要的才可以,否則就是偷竊,千萬做不得。稻穗給雞吃,雞生蛋,煎菜脯蛋帶便當,地瓜先給豬吃,如有剩的再換冰棒消暑。阿母為了我一本十塊錢的課外書,也要向鄰居先借來給我。我捨不得搭五分車(糖廠小火車),都是來回走十公里的路到麻豆街上,怎能不好好用功讀書?
鄉下的醫療資源貧瘠,記得村裡有一位朗大夫,我聽不太懂他的外省口音,長大後才知道他是軍中衛生兵出身。朗醫師人很好,沒錢看病可以掛帳。由於營養不良,阿母常昏眩起不來,為了省錢,將惠安宮主神媽祖婆請回家,問乩童喝符水,這是早期農村社會的巫術治病,有點迷信。
現在台南老家的洗手間即為以前的豬圈,比一.三八坪還大,養了四隻小豬。有一天我和父親看著小豬的長大,父親答應我只要考試拿到全校同年級的第一名,他要給我一百塊錢的獎學金,當年我才念初一。可能是口蹄疫,豬隻來不及長大賣錢就病死,好一陣子全家大小天天吃病死豬,連便當也是,而我的獎學金當然也沒了。阿母從電視上看到我的牢房照片,說以前家裡的豬圈都沒有這麼小,難怪她長夜裡會為我哭泣!
我已經失去了岳母,不能再失去阿母。但我心裡明白,阿母真的老了,當阿母的目屎乾了,再也等不到我回家的那一天,而我永遠聽不到「扁媽的呼喚」時,那才是我最害怕的!
source: 陳前總統辦公室,原載於:壹週刊590期陳前總統專欄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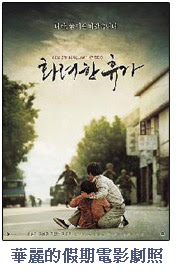




0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